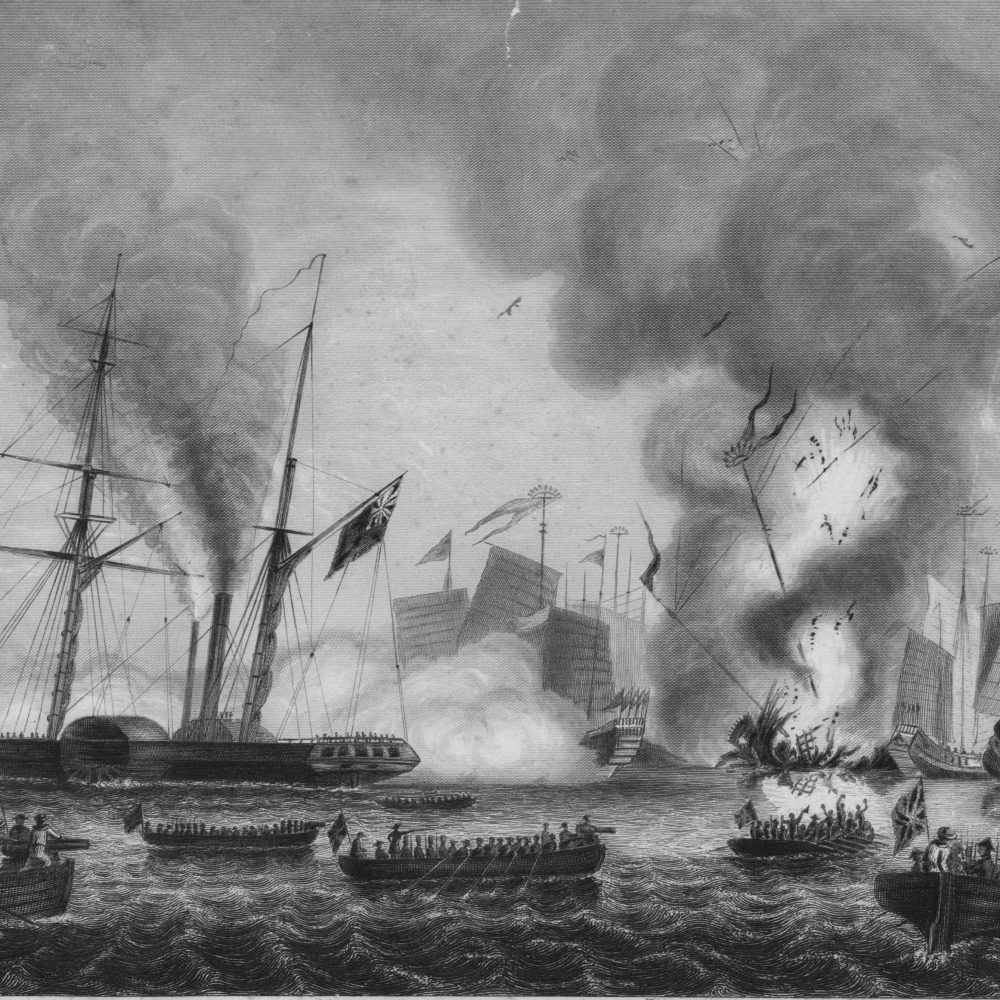刊登日期 : 2025-10-01
逃港潮,作為一個歷史名詞,記錄着一個特定的社會現象。上世紀70年代末,歷史上最大的逃港潮席捲了中國廣東沿海地區,許多群眾帶着大大小小的行李,湧向與香港僅一河之隔的寶安縣,試圖逃往香港。讓人們甘願背井離鄉逃往香港的原因,主要是因為兩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。
改革開放前 寶安縣與香港農民收入相差100倍
據統計,當時寶安縣農民的年收入僅為130元,而香港農民年收入卻達到1萬3千元,差距之大竟達百倍。
當時在廣東流傳着這樣一句話:「辛辛苦苦幹1年,不如人家8分錢」。這裏的「8分錢」,指的是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的郵資。於是,愈來愈多的人鋌而走險,蹈海求生。
紀實文學作家陳秉安指出:「到廣東來以後分3條路,中線就是走現在的梧桐山,直接經過深圳河逃到香港的新界;東邊就是游過大鵬灣;西邊游過我們附近這個深圳灣到香港的元朗、上水。」
愈演愈烈的逃港風潮引起了黨中央和廣東省委的高度重視。

習仲勳:惟有發展經濟 才能從根本上遏制逃港
1978年4月,習仲勳到達廣東出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。習仲勳離京南下之前,中央領導同志向他交代的任務之一,就是到廣東之後要抓緊解決逃港問題。
習仲勳馬不停蹄地深入基層展開調查。調研中,習仲勳深入邊境農村、哨所、口岸,親眼目睹了一邊是繁華熱鬧的香港,一邊是冷落蕭條的寶安。如此鮮明的對比,讓他感觸良多:「解放30年了,那邊很繁榮,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。」
實地調研讓習仲勳對發生逃港潮的根源有了清醒的認識,最終得出了「惟有發展經濟,才能從根本上遏制逃港」的結論。習仲勳對寶安縣的幹部說,要下定決心改變面貌,讓逃過去的人回到我們身邊。
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第三編研部主任閆建琪憶述:「那時候習仲勳同志在廣東工作,他有所考慮,怎麼利用毗鄰香港這個優勢,發展我們內地的經濟,而那個時候我們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,你怎麼搞對外加工貿易?怎麼搞『三來一補』?你得有特殊政策,得有靈活措施。」

廣東迅速推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遏逃港潮
在黨中央的支持下,廣東省迅速出台了一系列增加就業、提高收入、發展經濟及改善民生的措施,最終有效遏制了逃港潮。
事實上,上世紀70年代末,隨着全球經濟的快速發展,香港作為亞洲重要的自由貿易港推行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,在短時間內獲得了經濟的騰飛,成長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,被譽為「東方之珠」,與中國台灣、新加坡、韓國一起被稱為「亞洲四小龍」。
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武力表示:「香港這麼點兒的地方,這麼少的人口,在(20世紀)50年代的時候,它的這個國民經濟收入沒有廣東多;但到1977年的時候,它的進出口貿易超過了整個大陸,它進出口貿易大概是160多億美元,整個大陸才148億(美元),這你沒法比了,所以這種差距非常大。」
延伸閱讀:改革開放|袁庚與蛇口工業區 你聽過「時間就是金錢」嗎?
中國意識與發達國家差距大 急起直追
與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,1978年的中國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水平卻仍然徘徊不前。
美國記者的一篇名為《儘管宣布要對工廠進行改革 工作仍然鬆鬆垮垮》的目擊記,發表在1978年7月28日的《華盛頓郵報》上。這位美國記者寫道,中國一家工廠有2,500多名工人,在我逗留的幾分鐘裏只有1個人幹活,這種鬆鬆垮垮的工作態度,是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現現代化的一個主要障礙。
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王巧榮形容:「我們那時候意識到西方的發達,但是沒有意識到他們已經發達到這樣一種水平。那個時候最明顯的一個,當時有一個日本的記者來中國採訪,他就發現在我們的一個比較大的國有企業的一個工廠裏面,還有一台140年(前)的一個英國機器在那兒發揮着一個重要的作用,他就覺得很是不可思議的這樣一件事情。」(四之一)
(轉載自中國中央電視台《抉擇──1978》之《工作重心轉移》,標題及內容經編輯整理)
延伸閱讀:「抵壘政策」實施 移民湧入造就香港經濟